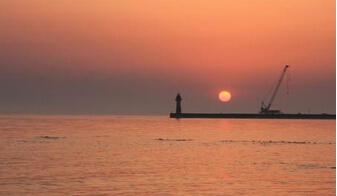
我是一个让老妈绝望到抓狂的孩子。
幼儿园上到中班,还不会擤鼻涕。每次,妈妈大喝一声:“擤!”我就希溜一声,使尽吃奶力气往里吸。这么一个简单的呼吸吐纳,就是学不会。
妈妈给了五块钱,让我出门买一斤盐。我听成买冰棒,狂喜之中狂奔上街。小贩子更觉喜从天降,把阔口保温瓶中的存货一下子清空。我用报纸抱着一堆冰棒,一颠一颠进门时,身上衣服与家门口,都黏成一片——冰棒几乎全化了。
不记得那时多大了,只记得老妈揍了我一身汗,然后又把我扔进木盆里洗澡。想想,还生气,在木盆里又揍了我一顿。五块钱,那个年代里,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碰到这样不吃打又没记性的破孩子,老妈很快就成了精细记录我劣迹的历史学家。
我老妈扬着手,学着我小时笨拙骗人模样,每一回都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我是个撒谎成性的家伙。也奇怪,我老妈家族里的人,似乎都有表演天赋,说话表情夸张,嘴里象声词也多。所以,我的劣迹,就这样在时间之河里生动地漂着,怎么泡也不褪色。
我从来认为,大人与孩子之间,完全是两个国家,有两套迥然不同的表达系统,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要讲尊严。而且,孩子的自尊可能比大人更敏感。
不知道为什么,我老爸老妈那一代人,几乎都是打击孩子自尊心的高手。我老妈似乎更有创意,算是打冷枪的神射手。
一个冬天,快上一年级的我,跟一帮小朋友在大院里窜来窜去,玩得正疯。我老妈洗着被单,忽然勃然大怒:“还玩!看看,你又尿床!大冬天的,洗被子容易啊!”
全体小朋友都愣住了。那一刻的安静,无比漫长。
洗好的雪白床单,很快晾在院子里。其实,私下里,小朋友们都知道对方尿床的事迹。问题是,有一面标志着我尿床的巨大白旗,在院子里飘着呢。
相当一段时间,在小朋友中,我就像被批判的坏分子,颜面扫地。
那个年代,护犊子的家长不多。小朋友要是打了架,大人都是各自把孩子揪回家,暴打一顿。然后,再把孩子叉出家门口,向对方家长亮出孩子的青紫伤痕,以示尽了教育之责。记得这种时候,相邻的两家,都会传出孩子的鬼哭狼嚎,杂以“跪下跪下”的呵斥声。不知道其他伙伴跪下没有,反正我每次只肯跪一条腿。我认为,跪一条腿不算跪。现在想来,那也算维持了一点畸形的尊严吧。
美国有一个叫弗罗姆的精神分析学家说:“如果不了解对方,那么想尊重就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以了解为指导,那么关心与责任就是盲目的。”我与小朋友们碰到的悲剧是,几乎每一个父母,都以为最了解自己的孩子;而且又认为,只要出自于关心与责任,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大概是小学二年级时,我偷了妈妈包里的钱,用途基本上是买了小人书。东窗事发后,我被勒令一星期不许上学。妈妈说,一个小偷,上学有什么用!一星期后,她想出了一个妙招,兼具惩罚与防范的双重功用:我的所有衣服裤子的口袋,一律用针线严严实实地缝上。
一个小偷怎么能有口袋呢?也就是说,我从此不配使用口袋。这个无口袋阶段,足有一年。大概妈妈也隐约觉得,缝口袋的创意有点出格,所以,这个耻辱的秘密,我得以小心维护了一年。后来,读美国小说《红字》,看到那个通奸的女人,被教会规定,胸前终生佩带着鲜红的A字。我心里说,幸亏老妈没读过这书。
弗罗姆说,爱首先不是同一个特定的人的关系,它是一种态度,一种性格倾向。这种态度、性格倾向决定了一个人同整个世界的关系。我想,每个人都是通过爱上几个人,来爱整个世界的。我老爸老妈的年代,世界实在太不可爱,大人国里的仇恨与鄙薄,远多于爱与尊严,怎么可能顾得上我们小人国呢?相反,他们潜意识里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倾向:通过对付小人国的问题,来解决大人国里的麻烦。
我老妈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也是一个严格执行计划的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切礼尚往来,都被她纳入不可更改的家庭计划中。
一天,她让我给街坊老刘叔叔送几个肉包子去。我又一次犯了极端粗心的错误,把包子错送到隔壁的尔辉叔叔家。路上,我还在想,是啊,上回,尔辉叔叔送了我们家大南瓜,所以妈妈这次就还他肉包子了。
近40年后,小学同学的名字,我一个也想不起来,却能清楚地记得邓尔辉这名字。原因就是,我陷入了一场可怕的外交危机。
本来,几个肉包子送错了,就将错就错吧。可是我妈偏不,她让我去把包子再讨回来。因为,尔辉叔叔的南瓜,已经用水饺还过礼啦。老刘叔叔的人情还欠着,你拿什么来还?老妈声色俱厉:“自己犯的错,必须自己挽救!”
天哪!这怎么可能?
我至今认为,这是自己一辈子遇上的最大难题。两家的关系不能搞坏,东西又必须索回。成年后,一看到陷入危机的国际关系,我就想起小时候碰到的外交窘境,总结了一个道理:在弱国与强国之间,尊严永远是拿来换取实惠的。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共有条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