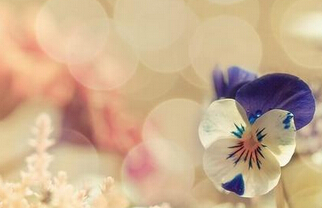
小学三年级时,我有一个男同桌,着实可恨,是个假姑娘。
我们这个江边小镇,女儿生得多的人家,忽然生个小子,会小心得像做贼,不敢堂皇拿出来当儿子养。于是,出现许多假姑娘。
假姑娘们,下课时,上厕所,上男厕所。放假时,跟小子们一道爬桑树,翻墙头,下河捉鸭子。
可是,再怎么猖狂,脑袋顶上会拖下一根乌油油的辫子。是几乎很耻辱的辫子。
男生女生谁不爽了,就冲着他们喊:假姑娘!假姑娘!假——
我就跟这样的一个假姑娘同桌。他皮肤很白,白而多肉,却没有姑娘的阴柔秀气之美。
下雨或下雪天,常常是他姐姐来接他。经常是不一样的姐姐,说明姐姐很多,说明父母很老,说明他在家里的地位。
三年级的语文课,刚开始学写作文,我写了篇《我的弟弟》。我采用总分总的结构,在中间部分依次写了弟弟调皮、懒惰、爱吃三大特点。因为有案例有分析有结论,行文小羊羔下山吃草一般,很是畅快,被语文老师当佳作当堂宣读。
我那天放学很得意,因为不仅收获了老师的赞扬,还有全班同学的羡慕。不想,刚放学,就被我弟弟举着拳头追。
是谁把鸡毛信送到了我弟的手里?
是假姑娘,我的同桌。
语文课一结束,假姑娘就跑到我弟的班上,跟我弟大肆渲染。说我弟被我写得声名狼藉啦,猪八戒都不如啦。
可想我弟有多恨。
全班同学听老师读作文,都在羡慕作者好文笔,只有假姑娘像颗变异的种子,听后去找文中的主人公,不仅考证,还趁机蛊惑人心。
假姑娘太阴了!我从此更加瞧不起假姑娘。咒他长大讨不到老婆。教室里只要有臭气,大家纷纷手捂嘴巴,交头接耳相问,谁的屁股没关紧?
我就指指假姑娘。我一看他,就像个关不紧的人。嘴巴都关不紧,都伸到我弟的班上去啦,屁股还能关得紧?
好在到了四年级,终于算是高年级了,政策适当放宽。
我在老师眼里,是最乖最聪明的,被安排和老师的侄女同桌。啊哈,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做人了。回头看见那些个子还没长起来的女同学,依然和男同学小夫妻似的坐一张桌子,吵吵闹闹,在桌子中间划楚河汉界,就好同情她们。
新学期,他好像忽然庄重起来了,不再和女生作对,穿蓝色黑色灰色的衣服,隐入男生的队伍里,和我们走得越来越远。
到中学毕业,我几乎彻底忘记假姑娘的存在。可是有一回过年,在小镇的超市里,一起排队付账时,竟遇到假姑娘。我看看他,他看看我,“你是……”“你是……”我们都手指对方的脸,大笑起来。他说出了我的名字,但我不敢说出他的名字,因为我从前从未叫过他名字,开口闭口都是假姑娘。
最后,他的省略号里终于补进去许冬林三个字,我的省略号就一直省略着。
他带他姐姐的孩子来买东西,抢着要把我的东西一块付账,我赶紧说我还没选好,做出往后退的姿势。
等我排队付账完毕,正要出超市,看见假姑娘还没走。假姑娘身边,我仔细侦察了一下,没有挨得特别近的真姑娘。难道假姑娘还没结婚?还没有女朋友?
假姑娘说:“等你呢,把手机号码给我哈,下次小学同学会,我喊你,你要来啊。”
我笑:小学,多么遥远啊,到底有哪些同学我早忘得以为是前世了。
我把号码报给他,他按手机,我的手机响,证明没错。
他就还像小学时候一样,写字时,一边写,一边念出声音,念出我的名字。
我呢,只能含蓄地,在一串陌生数字前面存下“假姑娘”三个字。我想,我以后只能被动地等,等他打电话时说出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不敢说:“嗨,是假姑娘吗?”
后来,回娘家,遇到一些已经嫁作人妇的小学女同学,跟他们提起假姑娘,零星获得一些信息。假姑娘已经谈过好几个真姑娘,可是奇怪,总是谈着谈着,就谈分了。假姑娘对人家真姑娘也够殷勤的,可是奇怪,越殷勤人家越不买账。
好像还结过一次婚,悄悄地,因为很快就离婚了,所以对外发布消息时只说没结过婚。
假姑娘的父母已经不在,所以每次过年,他都是跟姐姐在一起过。
假姑娘以前在羽毛球厂上班,后来在姐夫资助下,自己出来开过小公司,经营得很平静,一直没有什么大动作……
有一回,我正在外地进修,晚上接到假姑娘的电话。电话里有好悠扬的音乐声,然后是假姑娘的声音。假姑娘说:“喂,许冬林吗?”
“嗯,我是呢。你在哪呀?”我跳过了他的名字。
“我在听音乐会呢!”
“哦……”听音乐会也打电话跟人家说,好像是表白他有多么风雅,真土!我心里想。
“我在听《梁祝》!”
《梁祝》,《梁祝》我听得多了,多得像听儿歌,有什么可说的。我心想,继续“哦”了一声。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共有条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