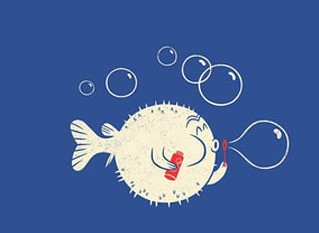
上课铃响,复旦大学古典诗词导读的课堂里挤进来一个男生,背着双肩包,找到教室中间的一块台阶坐了下来,拿出一个厚本子放在膝盖上,腰杆笔直。
在这个课堂上,他的身影并不陌生,每节课准时出现,一节不落。从哲学系张汝伦老师、中文系骆玉明老师,到管理学院谢百三老师,只要在校内很“火”的课堂上,一定能看到他。
他叫樊羽,原是深圳某大学的本科生,18岁决定休学到复旦旁听。两年间,从复旦到北大,他以“游学”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本科教育。
我怕学习热情会消失
两年前,樊羽考入了自己的大学,专业与金融相关。他的数学底子不好,被调剂去学数理统计,有些头痛。咨询了学长学姐的经验,发现在这里读到毕业,工作后的薪水扣除深圳生活的高成本以后,所剩无几。考虑到未来的生活,他的厌学之心更重了。
“最可怕的是上了大半学期课以后,我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想学习了。上课和考试都可以敷衍,看不到感兴趣的东西,学习热情慢慢没有了。人应该是要学到老的,但是如果现在就觉得学习是件痛苦的事,那毕业以后肯定也不会自己找书去读了。”
看着室友打游戏,坐在课堂上发呆,时间匆匆而逝,他想逃走。在上海转过一圈后,他决定来复旦旁听。当被问及决定时是否纠结过,他说,“没有纠结,你觉得别人为什么会纠结?”
樊羽的小学和初中同学知道他的选择后,一点也不诧异,觉得这就是他能做出来的事。
小学五六年级,每次老师提问,如果大部分同学都会选A,只有两三个选B,他一定是那两三个之一,“错的那两三个,是我;对的那两三个,也是我。不是故意的,我当时真的就那么想的。”
从小爸妈对他的教育相对自由,几乎每个假期他都不会老老实实在家呆着。记得有一年放假,他想起家里来过一个叔叔,住在他没去的城市,就跟爸爸请示自己去他家玩,后来联系了一下,就去了。
能出来“游学”,樊羽最感谢的人就是父母,他们在经济上支持他,容许他走自己想走的路。虽然妈妈始终有些担心,但爸爸和姐姐坚决支持,“男孩子就是应该出去闯闯,见见世面。”
只听名师的课
在上海和北京,他都租房住在学校附近,600块每月,但是北京条件更差些,三四个人挤在15平米的隔间里——虽然家庭条件还可以,但樊羽每月的生活费控制在1500元左右,和普通在校大学生差不多。
初到上海,他只认识姐姐在复旦读研的大学同学,她推荐了哲学系名师张汝伦教授的课,“一听,真的很好”,接下来从《国学概论》到《四书精读》,他连着听了张老师三学期的课。
像这样听一个老师的课两学期以上,在樊羽的课表中并非独此一例。还有中文系骆玉明老师和哲学系王德峰老师,前者讲古典诗词和魏晋风度,后者讲哲学导读和大学精神,樊羽听得很投入,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
在复旦,长期旁听的人大都会对人文学科某些老师的精彩授课有无穷的兴趣。樊羽在课堂上会经常遇到另一个旁听生董健,他从复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工作几年后,辞职回来旁听,只学历史、地理、中文等人文学科的课,到现在已旁听多年,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去埃及旅行。
旁听生们在逃离了功利主义的学分等土壤后,希望在人文名师的课堂中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沉淀和满足。这些极少数主动求学的“游学”者,作为一种提醒的力量,给校园内为了文凭奔波的大多数带来了无法避免的冲击和反思。
从复旦到北大,都有很多知道他经历后愿意帮助他的学生,“他们觉得,嗯……用他们的词,是‘羡慕’。”
在朋友的推荐下,樊羽不断充实着自己的课表。哲学、中文、历史、经济、管理、政治……什么专业的课他都有兴趣去听,只要老师讲得好。每学期,他固定去听的课程有10门之多,还有六七门偶尔去听,连双休日都排满。两年下来,如果算学分,他已经可以本科毕业了。
同时,他也积极地去参加同济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各种活动和讲座,业余时间排得很满。到北大后也依然如故,参加社团活动,饱览北大百年讲堂的话剧和音乐会,临走的时候,手里还刚买了孟京辉的话剧票。
当然,“旁听”他也有自己的重点。
到北京后,樊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哲学、国际政治和企业管理上。“我喜欢学企业管理,因为觉得这个最实在,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自己去实践;而且我家是做生意的,这样也可以帮到家里。”
他也喜欢听人民大学管理学院包政老师的课,他被誉为经管类咨询师第一人,MBA的学生都抢选他的课。包老师讲课风格深入浅出,让始终对管理感兴趣的樊羽颇为受益。
旁听生的江湖
自1898年创办京师大学堂至今,旁听生就是北大校园内的一个常见群体。任继愈先生曾这样回忆老北大的旁听生,“当时北大校门任人出入,教室任人听课,图书馆阅览室也任人阅读。不管是不是北大的成员,都可以走进来,坐下就看书,无人干涉。”老北大旁听生的名气甚至不在正规生之下,比如沈从文、胡也频、丁玲、冯雪峰、柔石等。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共有条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