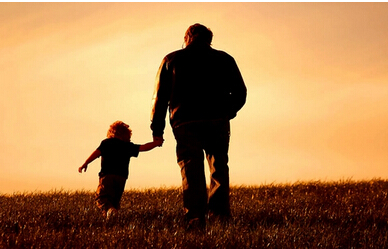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可以好到不计回报,天下除了父母还有谁能做到呢?
遇到他那年,我17岁,他47岁。
17岁的我,把头发烫得像盛放的牡丹,涂紫色的眼影,装模作样地叼根烟,跟一群不良少年混迹在夜店里。课旷得多了,老师就给我打电话,我很嚣张地笑:“不就是请家长嘛!又不是第一次,你看着办好了。”老师软软地说:“叶小羽,你这样对得起……”我知道她会说什么,很快挂了电话,继续喝酒,可是心里却酸酸的,很难受。
从酒吧出来,已经凌晨3点多了,我喝得醉醺醺的,忽然就看到他站在不远的树下,穿得像只甲虫。他徘徊着走过来,声音抖抖的,指着我说:“你,叶小羽,给我过来。”
我傻了傻,没想到他会到这里来。男生们问我:“叶小羽,你爸呀?”我说不是。他们喝了酒,正在四处滋事,一听便来了劲儿,捋着袖子将他团团围住。他站在中间,矮矮的个子,穿着街边小摊买来的劣质羽绒服,一脸惊恐地望向我。我刚背过身,便听到他压抑的、痛苦的呻吟。我镇定地离开,强忍着没有回头。
是的,我恨他。很多夜里,我想着父亲,便流着眼泪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还狠狠地诅咒他。可是今天,我远远地看着他佝偻成一团,腰弯得像只虾米,落寞地往回走,我心里却涩涩的,并没有预想中的开心。
第二天,我酒醒了些,回想起来有些后悔,便窝在家里不敢出门,直到那晚的朋友打来电话,说他伤重住院了。大家央求我去看看他,主要是去息事宁人,希望他不要报警。
我去医院时,带了些自己胡乱做的皮蛋瘦肉粥。我在病房门口徘徊,他看到了,就在病床上嘿嘿地笑:“是小羽吗,快快,进来啊,拎的什么,哦,好香啊!”记得我第一次做饭,父亲也是这样,面对着一桌子难以下咽的东西,装出一脸的惊喜。可他不是我父亲,我忍住泪,狠狠地看着大口吃东西的他,心里的恨难以消除。
我高三那年,他停了出租车,在我家隔壁租了房子住下,开始做我的保姆兼保镖。他买来菜谱,围上围裙,做好饭就敲我家的门,傻傻地说:“尝尝,小羽,我新创的,看可不可口。”他还时不时地把来找我的社会青年赶走,我站在窗口,看着这个矮小的男人内心胆怯却故作勇敢,大声呵斥他们:“我家小羽就要高考了,谁敢乱来,别怪我不客气啊。”有男生笑他:“你是她什么人,管得着吗?”
他义正词严,表情严肃:“我是她爸。”
为此,我和他大吵了一架。我的手几乎指到了他的鼻尖,声音尖厉:“陈建生,不要忘了你对我家做过的事,我告诉你,谁都可以做我爸爸,除了你。”回家时,我把门摔得轰响。过了一会儿,我听到隔壁传来他“哇哇”的大哭声,像个孩子一样。我看着父亲的照片,他仍是微微地笑着。我把头深深地埋下,听着隔壁的哭声,也哭了。我不知道自己这么做对不对。
我一如既往地躲着他,他怕我变坏,也一如既往地跟着我。我的头发越来越长,黑黑地盖住了那些花花绿绿的颜色,劣质的眼影让我的眼睛疲惫不堪,我只好把以前的黑框眼镜戴上。偶尔他看我久了,会憨憨地说:“小羽,我第一次见你,就是这样的好孩子形象,也不说话,就那么乖乖地看着我。”我挑衅地看着他:“那你也还记得是什么场合吧……”我们的短暂谈话便戛然而止。我的话刺伤了他,看着他受伤离去的身影,我的心里有轻微的快感。
是的,我似乎永远都那么恨他,不管他为我做过什么。
在他的“监管”下,我勉强升入了一所专科学校。转眼毕业了,我就在这座城市扎下根来。家还是那么大,走在中间,空落落的。父亲的照片还在,人还是微微地笑着。镜框擦得很干净,一定是他常来帮我收拾屋子。他还住在我隔壁租来的屋子里,干起了老本行,早出晚归地跑出租。我们很少见面,见到了,也很少说话。我不理他,他老了,话也少了很多。
我认识了一个男孩子,叫刘肖。在酒吧里,他看我埋头喝闷酒,就带我去跳舞。强劲的音乐,闪烁的灯光和疯狂的摇头摆尾让我暂时忘记了所有不快。约会几次后,我带刘肖回家,他死死地守在门口,就是不让我开门。
时间似乎倒流到了几年前,他脸上还是怯怯的表情,声音抖抖的,指着我说:“你,叶小羽,给我过来。一个女孩子,像什么话!”刘肖问:“你爸呀?”我说不是。我喝得醉醺醺的,酒气喷了他一脸,我说:“我就是没教养的女孩子,怎么了?可是,是谁让我爸死那么早的?”我的话永远带刺,他不眨眼睛地看着我,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我的心突然有了一丝柔软。
从小到大,我从来没见父亲哭过。可却见他哭了两次,眼泪鼻涕横流,哭得像个孩子。
而且,每次都是因为我。
后来我和刘肖分了手。他说的对,刘肖不是个好男孩。他喜欢赌博,每次输了钱就去酒吧喝酒。我说分手,他不同意,还醉醺醺地说:“叶小羽,你家的事我打听过了,几年前的车祸,那老头赔了你不少钱吧?”我瞪着他,心像被锤子狠狠地敲了一下,脑袋里也轰轰作响。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共有条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