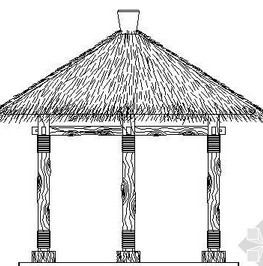
北风一吹,草就瘦下来。在冬天,草像老人一样,喜欢扎堆,在阳光下晒时光。
我是在公园邂逅冬天的。几个老人,坐在和他们一样老的草地上,谈着更老的事。冬天使时间变得迟钝,有些老,有些旧。父母也这样老了,那身老棉衣,把时光和容颜都穿旧了,但他们身手矫捷,割草翻地,总有忙不完的活。
忽然,就想家了。“三十而立”,我而立没立。一个奔三的男人,站在街头,两眼湿漉漉地想着家,让人倍感羞耻。还好没人发现,还好父母经营的家,永远都给我留着一扇门。
门是虚掩的。我从厢房到堂屋,从西间到东间,打开柜门,拉开抽屉……我不是寻找什么,只是想看看,他们是否还在原来的地方。院子里,响起鸡鸭的欢呼声,我知道是母亲回来了。我不好意思探出身,母亲看见我,愣了愣:回来了。
母亲靠门站着,门上的伤痕已无迹可寻。上次,因为我的婚事,我们大吵一场,我赌气摔门而出。母亲扬言:不结婚就不要回来。我回应:不回来就不回来。但我又食言了。或许因为我的反复食言,使母亲在我面前的时光,显得消化不良。
母亲拘谨地搓着手,倒杯热水:焐焐手,天冷。我捂着茶杯,一股暖流瞬间覆盖住我。我想说些什么,却说不出来。我捋着母亲蓬乱的头发,摘下草屑。时光就像荡秋千,小时候母亲做的事,现在轮到我做了。我试图拔尽母亲的白发,但那些老去的时光太多,我竟然无能为力。母亲老了,她正在老去的时光里一点点老去。
我四处寻望。母亲说,在南湖扒茅根呢。我这才意识到,我在找父亲。我说,我去搭把手。母亲笑笑,开始喂那些聒噪的鸡鸭。恍惚间,时光又回到多年以前。
在坑沿上,父亲的腰弯得比草还低。那么锋利的风,都无法挨近父亲。父亲撇下棉袄,高扬着锄头,浑身热气腾腾。看见我,父亲停下来:回来了。我嗯一声,缩手缩脚拿过锄头:我扒一会。父亲看看我,笑笑。在他眼里,我还是那个弱不禁风的孩子。
我赌气扬起锄头,扒得虎虎生风。很快,我就偃旗息鼓了。父亲是对的,我不是这块料。我蹲在父亲身边,捡摘土里的茅根。我没想到,土壤竟很温暖,像父亲粗糙的笑脸。那些白白胖胖的茅草根,像熟睡的孩子,蜷缩在泥土里酣睡。
见到妈了?父亲问。我点点头。父亲说:别和她斗气了,现在你也安顿下来了,该考虑结婚了,做父母的不就图这个……我望向别处,满坑的茅草,干瘦如柴,随着风,贴着地,蹒跚在时光里。草瘦为根!谁能想到,它们怀里酣睡着白胖的茅根。
父亲让我回去,帮妈烧锅,他再干一会。我问弄那么多干吗?父亲说:茅草可以扎扫帚,茅根可以做药,卖点钱,帮你交房贷。我没吱声,很想哭。《诗经》里说: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或许,我们一起错了。我要经营的不只是四方,还应有家,有父亲,有母亲。“何草不玄?何人不矜?”,我真的该成家了。
我背着茅草,父亲背着茅根。我们都走得小心翼翼,就像父亲背的是我,我背的是父亲。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共有条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