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的时间,我都爱着我的父亲。很长的时间,我都以为我不爱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是很英俊的。家里有老旧的黑白照片作证:那确实是一个好看的男人,轮廓深刻,浓眉大眼,端正而明亮,有一种坚忍的气质。站在机床前,自信而满足,微笑着,全无磨砺和疲倦的痕…
当老黄车祸的死讯传来,每个熟识的人,都流下了同情之泪。多惨哪!上天为什么那么残忍呢?如果死的是老黄的女儿小咪,老黄还能活下去,甚至重新振作,活得更好。偏偏死的是老黄,这是一场车祸两条命啊!小咪怎能不死?小咪是要死了。不论老黄死不死,小咪都已经到了死亡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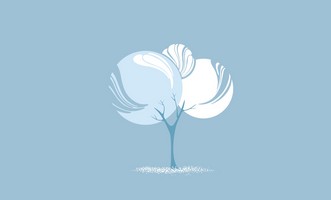
我和你分别以后才明白,原来我对你爱恋的过程全是在分别中完成的。就是说,每一次见面之后,你给我的印象都使我在余下的日子里用我这个愚笨的头脑里可能想到的一切称呼来呼唤你。比方说,这一次我就老想道:爱!爱啊!你不要见怪:爱,就是你啊。你不在我眼前时,我面前就好…

他和她约好了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到民政局领取结婚证,她问他为啥要这么早,他调皮地笑着说:“我们要抢个第一,要做明天第一对领结婚证的新人!”她笑着同意了。但到了第二天,她住的那条街道修路,她坐的车堵塞了许久才出得来,时间已经快九点钟了,她快…
小时候,我很崇拜自己的父亲,觉得他无所不能,只要我搞不定的事情,他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父亲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设计、绘图、预算、施工、结算,每一样他都亲力亲为,参与建设了很多优质工程。我很为自己有这样能干的父亲骄傲。我会指着路边的高楼对别人炫耀:&ld…
两腿做马步状,轻微弓起腰。儿子对躺在搓澡床上的父亲说,爹,今天我来给您老搓澡。父亲点点头,眼中似有泪水涌出。这是一家高档桑拿洗浴中心,父亲从来没有进去过,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到这里洗澡。沁水湾的庄稼人都和父亲一样,要么在村边的小澡堂里泡大池,要么用家里的太…

一林冲刺配沧州,行至野猪林,被董超、薛霸绑在树上,要加以杀害的时候,只听得松树背后雷鸣一声,一条铁禅杖飞将出来,把薛霸的水火棍一隔,飞出九霄云外,松树后面跳出一个胖大和尚来,林冲睁眼一看,正是他的兄弟鲁智深!原来,鲁智深“忧得你苦”、…
6岁时,费德林跟母亲来到巴西的一个小镇上居住。他从小就酷爱小提琴,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练上好几个小时。可不幸很快降临到这个小男孩儿的头上——附近的一家大型化工厂突然发生化工原料泄漏事故,费德林受到了影响。开始,他不停地呕吐和发烧,后来医…
有多少回了,我都想象一个场景:在村里的街上,遇见爹娘,说几句话,而非多日不见的牵挂;只是淡淡几句,诸如啥时浇地啊、卖不卖粮食啊。真的没什么可以格外在意的,因为过不了多大会儿,就又会遇上;或是端着刚煮熟的饺子,紧走几步送到爹娘的院子里。在我二十岁之前,生…
那堵墙,是阳光最多的地方。就像一湾被截流的河,时光暗涌,阳光波光粼粼。墙很老了。爷爷靠过,早已老去;父母靠着靠着,也老了。人老后,身体会出毛病,墙也是。墙基是土夯的,中间的青砖、红砖,是时光的补丁和创膏贴。与老人一样,墙的腰挺不直了,斜拄着一根&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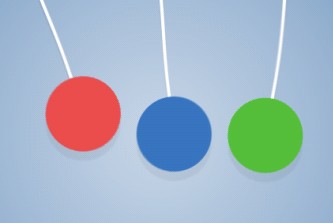
手扶住窗棂,我的心突然发疼。这是一个普通的夜,白天刚下过阵雨,风特别湿润,犹如海的呼吸,轻悄地穿过荒芜的花园,抚摸了我一下,脸上一阵凉意。是什么使眼睛发潮?为什么会想起你?窗外黑黝黝的屋脊,像几头卧鲸。深深浅浅的灯光,似乎要从万千人生故事中,泄露一点什…
那天夜里,我很晚回家。他们对我说,父亲过世了。我心头一阵刺痛。凌晨2点,我来到他的房间,想看他最后一眼。“他在后面那个房间。”他们说。我走了进去。几小时后,我在晨光熹微中回到了瓦里克纳吉大道,尼尚塔石空无一人,格外清冷寂寥。与我擦身而…